目录
快速导航-
抗战胜利80周年专栏 |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:一个政治概念的生成与发展
抗战胜利80周年专栏 |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:一个政治概念的生成与发展
-

抗战胜利80周年专栏 | “包而不办”与“办而不包”:国共两党在第三厅的角力
抗战胜利80周年专栏 | “包而不办”与“办而不包”:国共两党在第三厅的角力
-

抗战胜利80周年专栏 | 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信息传递
抗战胜利80周年专栏 | 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信息传递
-
革命史论 | 中共对香港的战略认知与实际运作(1921—1945)
革命史论 | 中共对香港的战略认知与实际运作(1921—1945)
-
革命史论 | 中共七大组织报告的设置与更迭及其影响
革命史论 | 中共七大组织报告的设置与更迭及其影响
-

革命史论 | 蒋介石对安平事件的反应
革命史论 | 蒋介石对安平事件的反应
-
建设史论 | 国营企业试建厂矿同志审判会的历史考察
建设史论 | 国营企业试建厂矿同志审判会的历史考察
-

建设史论 | 20世纪50年代中共对工人工资水平政策的探索与调适
建设史论 | 20世纪50年代中共对工人工资水平政策的探索与调适
-
建设史论 | “群众”是如何“阅读”的
建设史论 | “群众”是如何“阅读”的
-

改革史论 | 缓和“书荒”:1977一1980年图书出版工作的经困
改革史论 | 缓和“书荒”:1977一1980年图书出版工作的经困
-
粤港澳历史 | 新中国初期广东农村传统互助合作及其改造
粤港澳历史 | 新中国初期广东农村传统互助合作及其改造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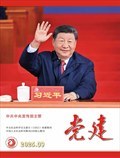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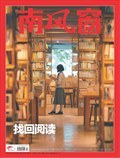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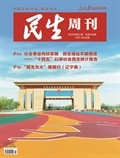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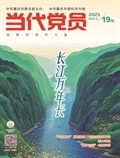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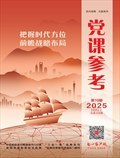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