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全部分类/
- 文学文摘/
- 小品文选刊·印象大同
 扫码免费借阅
扫码免费借阅
目录
快速导航-
卷首 | 书,不是为了完成任务
卷首 | 书,不是为了完成任务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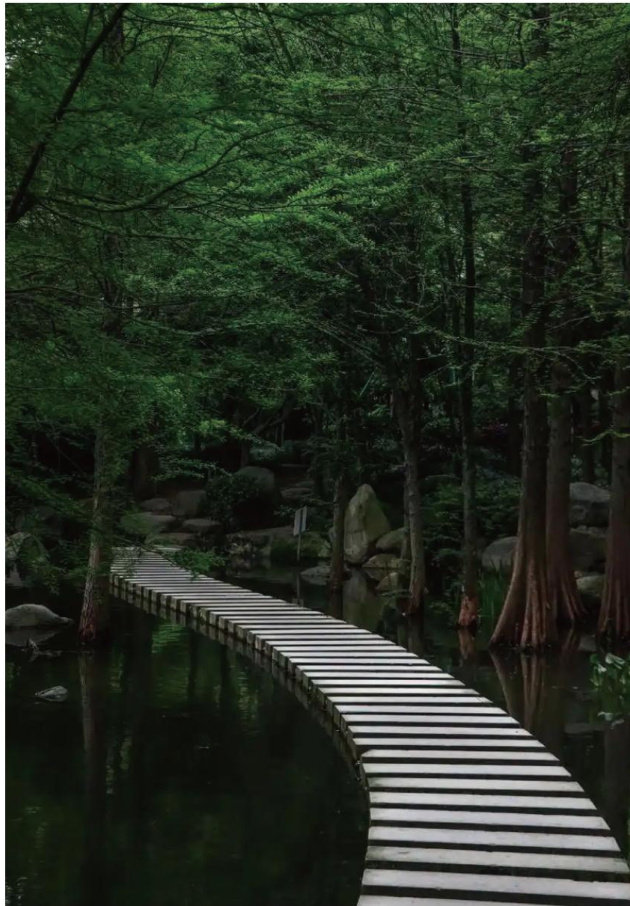
视野 | 曲径通幽的径与幽
视野 | 曲径通幽的径与幽
-
视野 | 湿地花影里的归途
视野 | 湿地花影里的归途
-

视野 | 壶口的风
视野 | 壶口的风
-

视野 | 栖心文瀛畔
视野 | 栖心文瀛畔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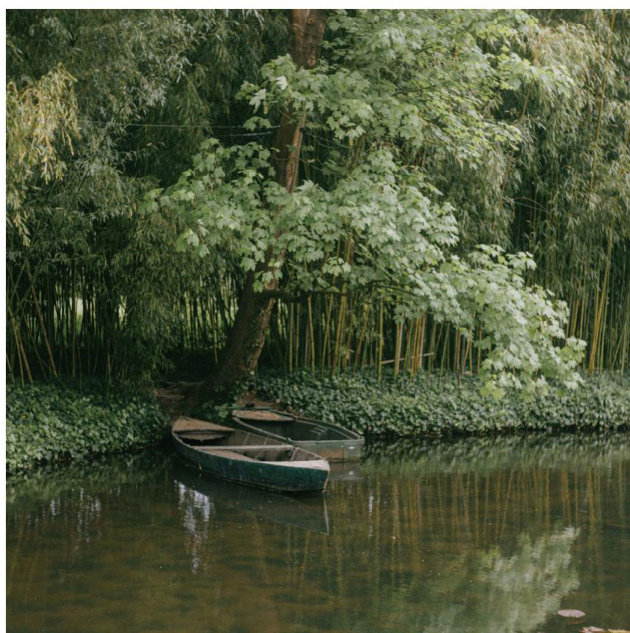
百态 | 讲一个关于“正义”的故事
百态 | 讲一个关于“正义”的故事
-

百态 | 十五岁那年
百态 | 十五岁那年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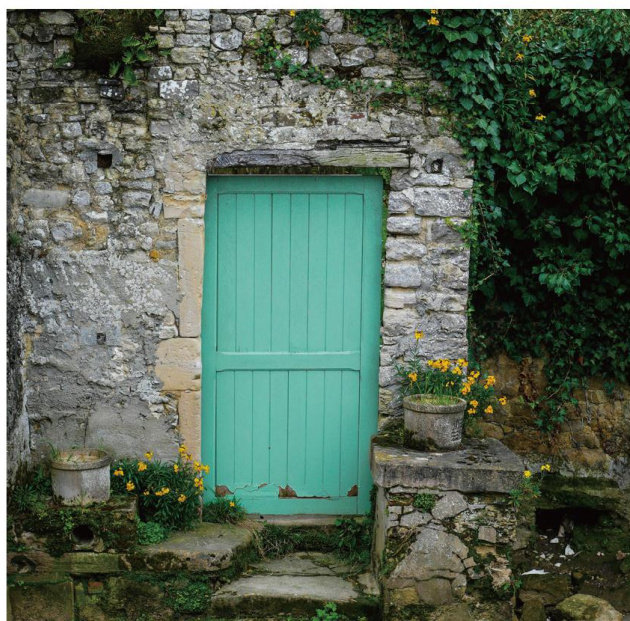
百态 | 喝得很慢的土豆汤
百态 | 喝得很慢的土豆汤
-

百态 | 母亲蒸的包子
百态 | 母亲蒸的包子
-
城坊 | 小巷
城坊 | 小巷
-

城坊 | 寻味大同
城坊 | 寻味大同
-

城坊 | 大城市里的死与生
城坊 | 大城市里的死与生
-

城坊 | 炊烟里的世相
城坊 | 炊烟里的世相
-

感悟 | 不朽的失眠
感悟 | 不朽的失眠
-
感悟 | 我做了教授
感悟 | 我做了教授
-

感悟 | 要是没有嫁给你(外一章)
感悟 | 要是没有嫁给你(外一章)
-
感悟 | 跟着花卉学写作
感悟 | 跟着花卉学写作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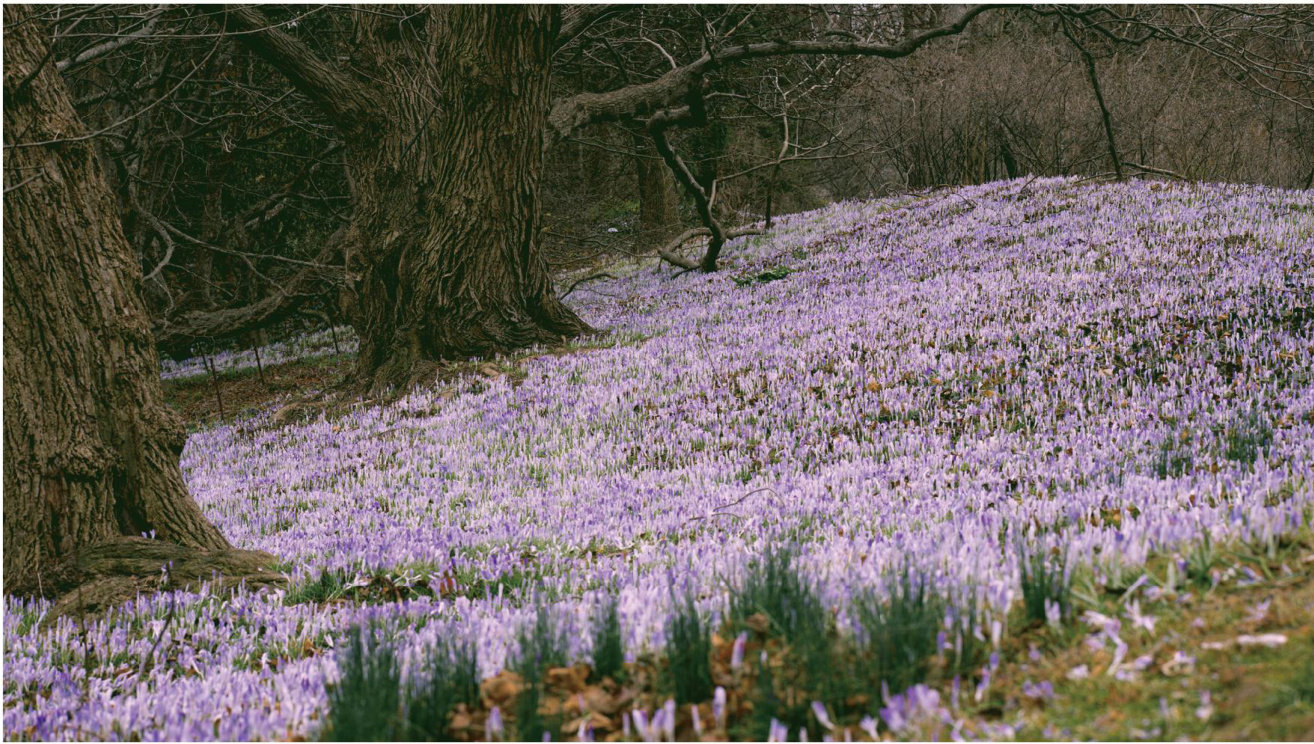
知道 | 这时候,你才算长大
知道 | 这时候,你才算长大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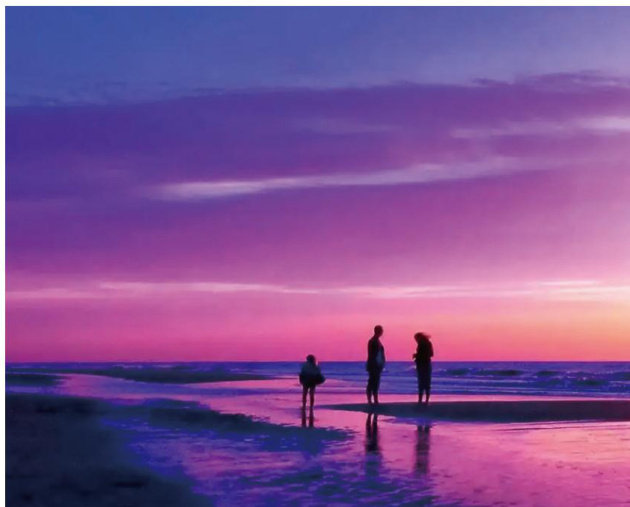
知道 | 带孩子四处旅行有意义吗
知道 | 带孩子四处旅行有意义吗
-

知道 | 什么是自由的人生
知道 | 什么是自由的人生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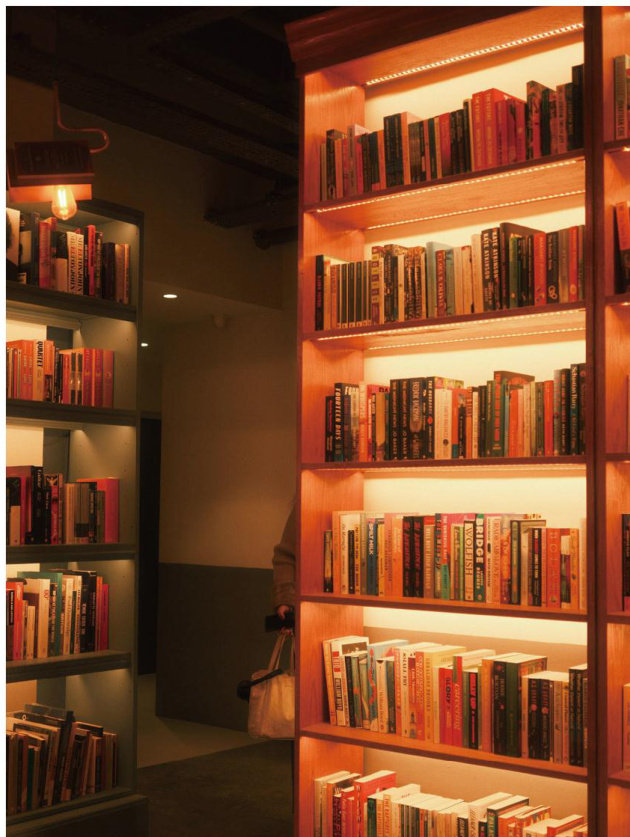
思维 | 读书育心智
思维 | 读书育心智
-
思维 | 我有的是时间
思维 | 我有的是时间
-

思维 | 渡过塞壬出没的水域
思维 | 渡过塞壬出没的水域
-

思维 | 生命与名利
思维 | 生命与名利
-
边声 | 我的眼睛只是个小小窗口
边声 | 我的眼睛只是个小小窗口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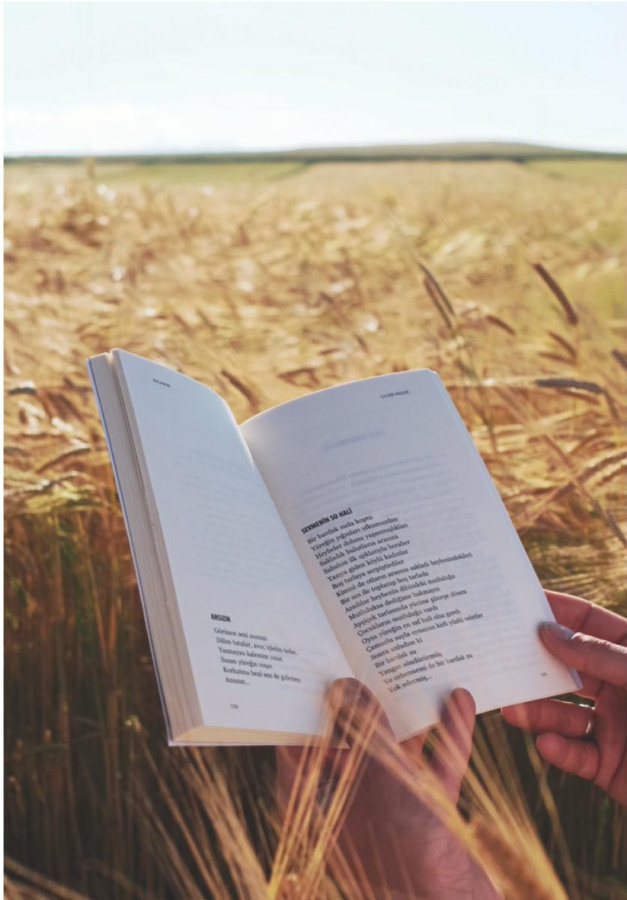
边声 | 让灵魂在圆融的世界徜徉
边声 | 让灵魂在圆融的世界徜徉
-
边声 | 仙人坑里莫干茶
边声 | 仙人坑里莫干茶
-

边声 | 打马黄河边
边声 | 打马黄河边
-
大同大不同 | 风云得胜堡
大同大不同 | 风云得胜堡
-
大同大不同 | 平城,公元五世纪的光荣与梦想
大同大不同 | 平城,公元五世纪的光荣与梦想
-

大同大不同 | 唯有平城多忍冬
大同大不同 | 唯有平城多忍冬
-
大同大不同 | 大东街的那棵大槐树
大同大不同 | 大东街的那棵大槐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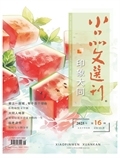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