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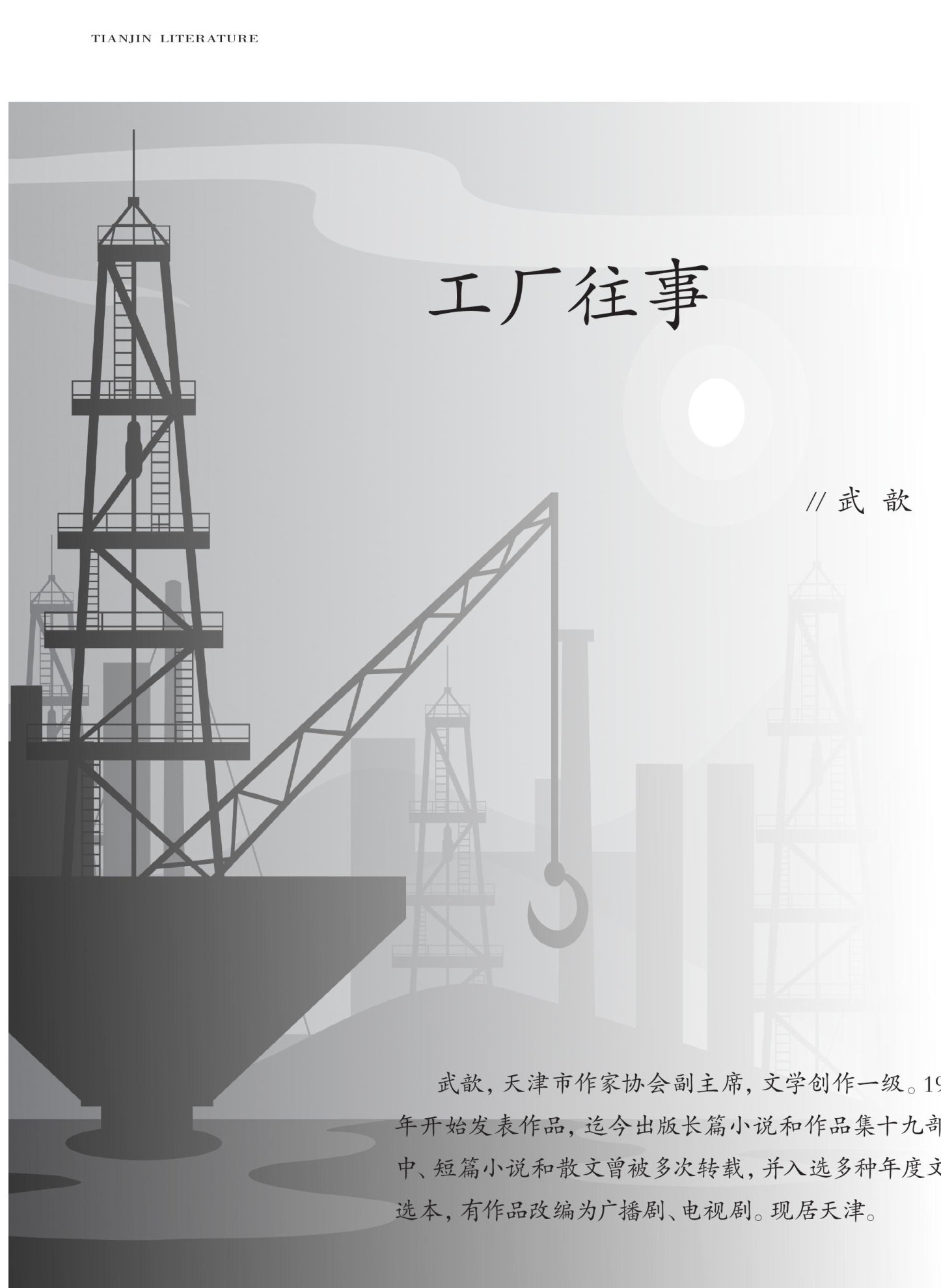
特稿 | 工厂往事
特稿 | 工厂往事
-

运河津韵 | 天津是个好地方
运河津韵 | 天津是个好地方
-

运河津韵 | 人间河流(组诗)
运河津韵 | 人间河流(组诗)
-
运河津韵 | 流淌在运河上的“津味”
运河津韵 | 流淌在运河上的“津味”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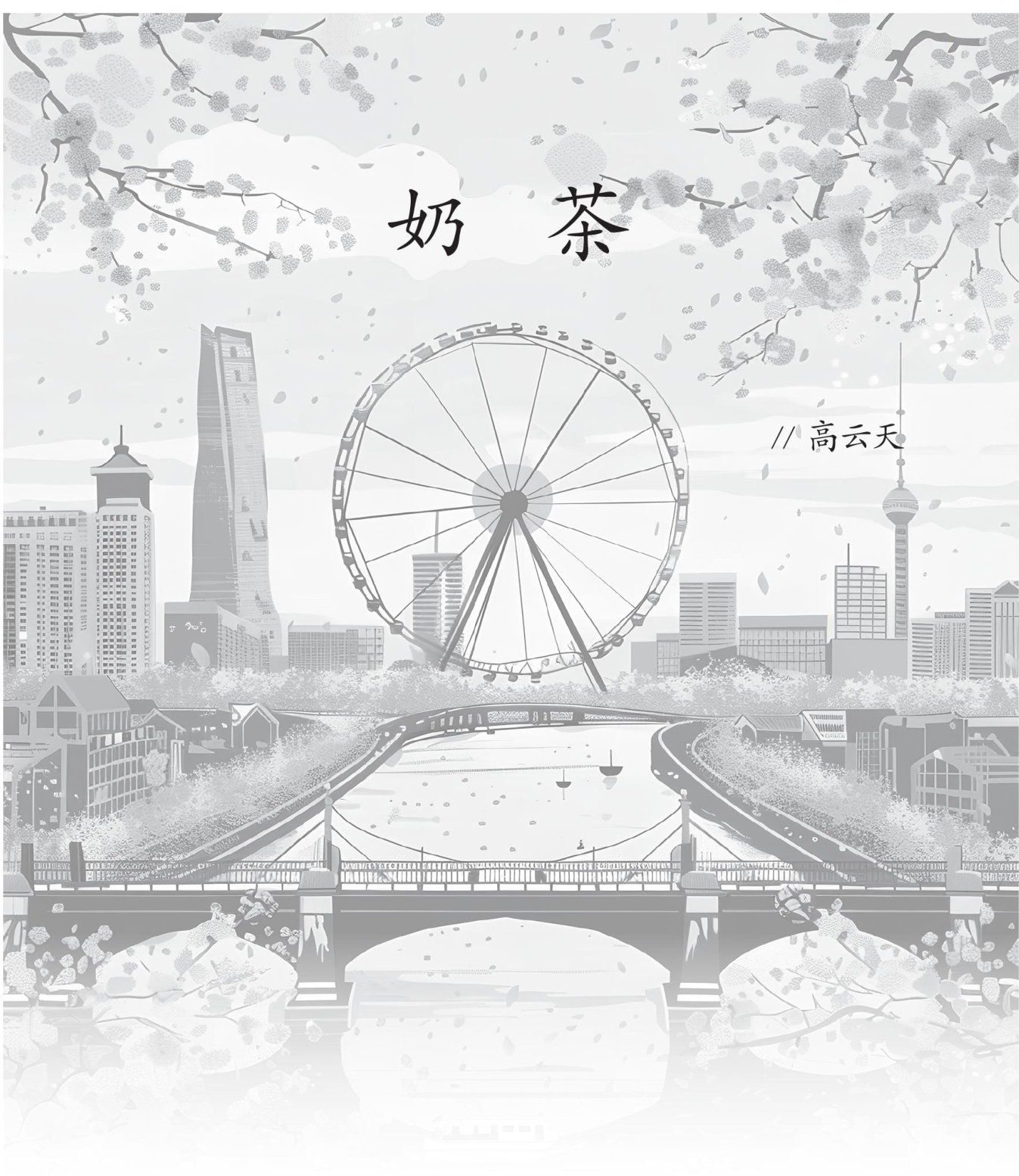
新实力小说家 | 奶茶
新实力小说家 | 奶茶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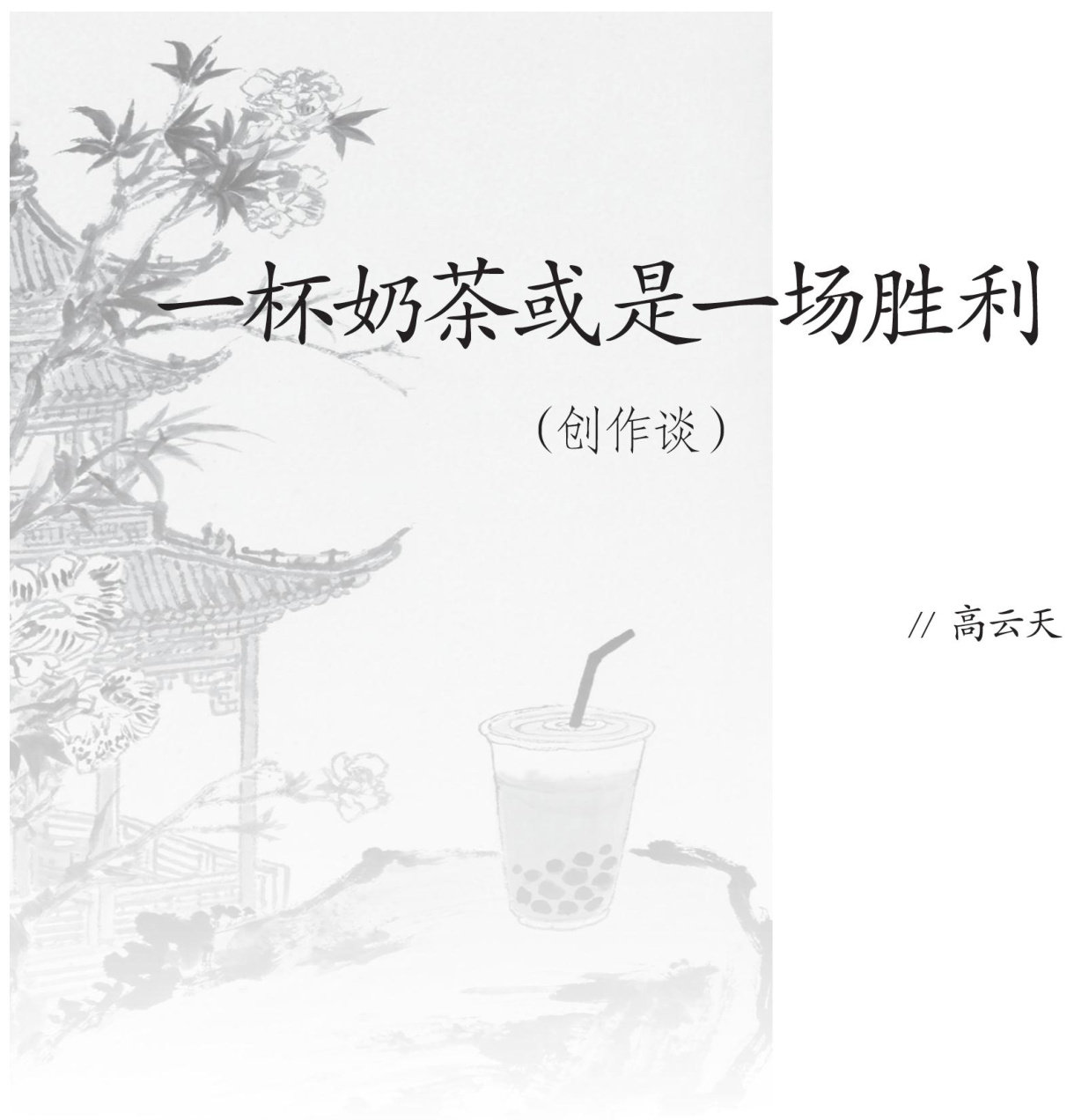
新实力小说家 | 一杯奶茶或是一场胜利(创作谈)
新实力小说家 | 一杯奶茶或是一场胜利(创作谈)
-

新实力小说家 | 在时间的缝隙里重写“本城”故事
新实力小说家 | 在时间的缝隙里重写“本城”故事
-
小说 | 生意兴隆
小说 | 生意兴隆
-

小说 | 逆猫
小说 | 逆猫
-

小说 | 三友
小说 | 三友
-

散文 | 一跃入海
散文 | 一跃入海
-
散文 | 明月光里忆诗魂
散文 | 明月光里忆诗魂
-

散文 | 麦芽糖放在柴垛上(外一篇)
散文 | 麦芽糖放在柴垛上(外一篇)
-
诗歌 | 牵牛花的梦(外一首)
诗歌 | 牵牛花的梦(外一首)
-
诗歌 | 养在指尖的光 (组诗)
诗歌 | 养在指尖的光 (组诗)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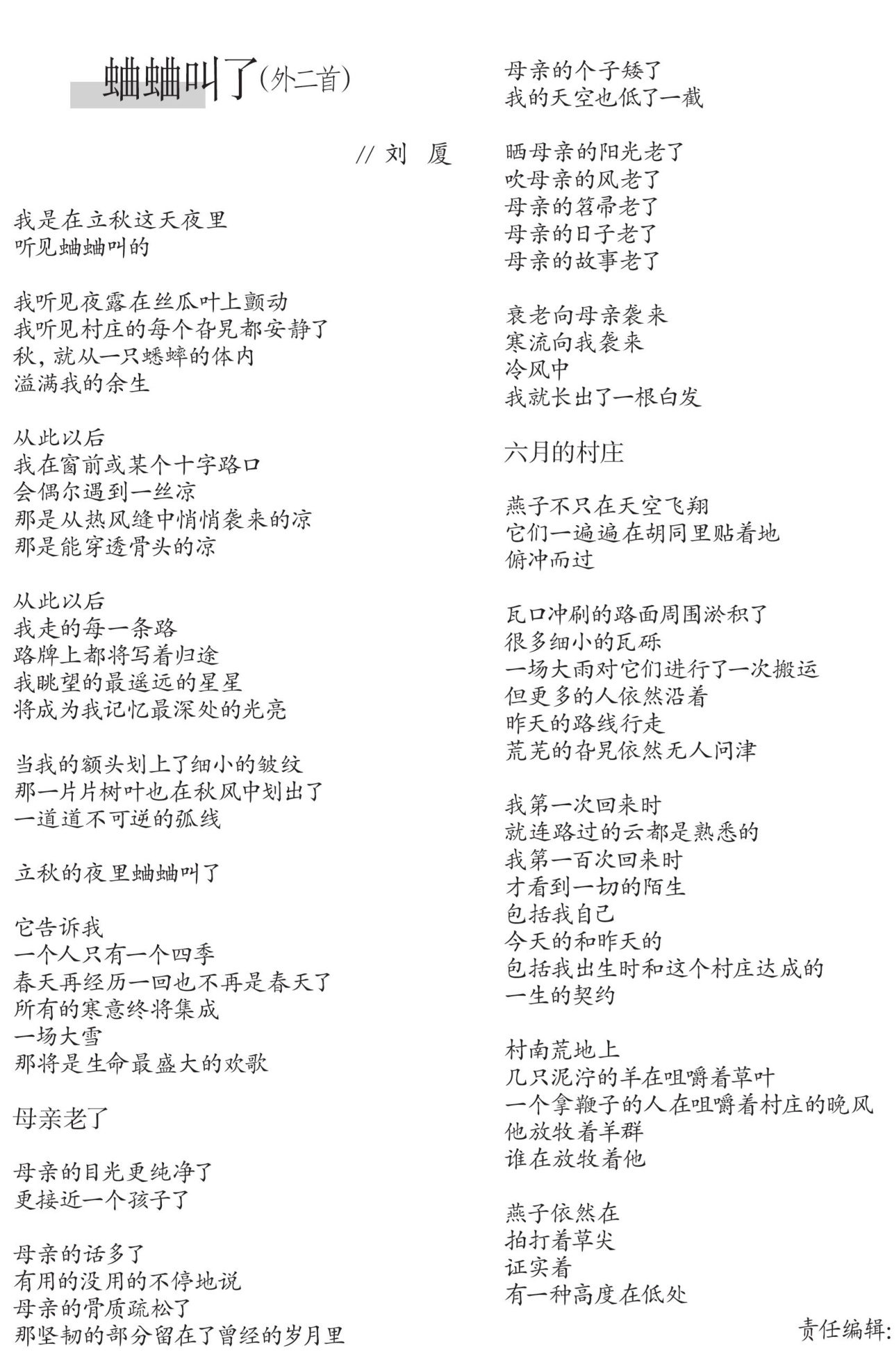
诗歌 | 蛐蛐叫了(外二首)
诗歌 | 蛐蛐叫了(外二首)
-
诗歌 | 月光和时光的守候 (组诗)
诗歌 | 月光和时光的守候 (组诗)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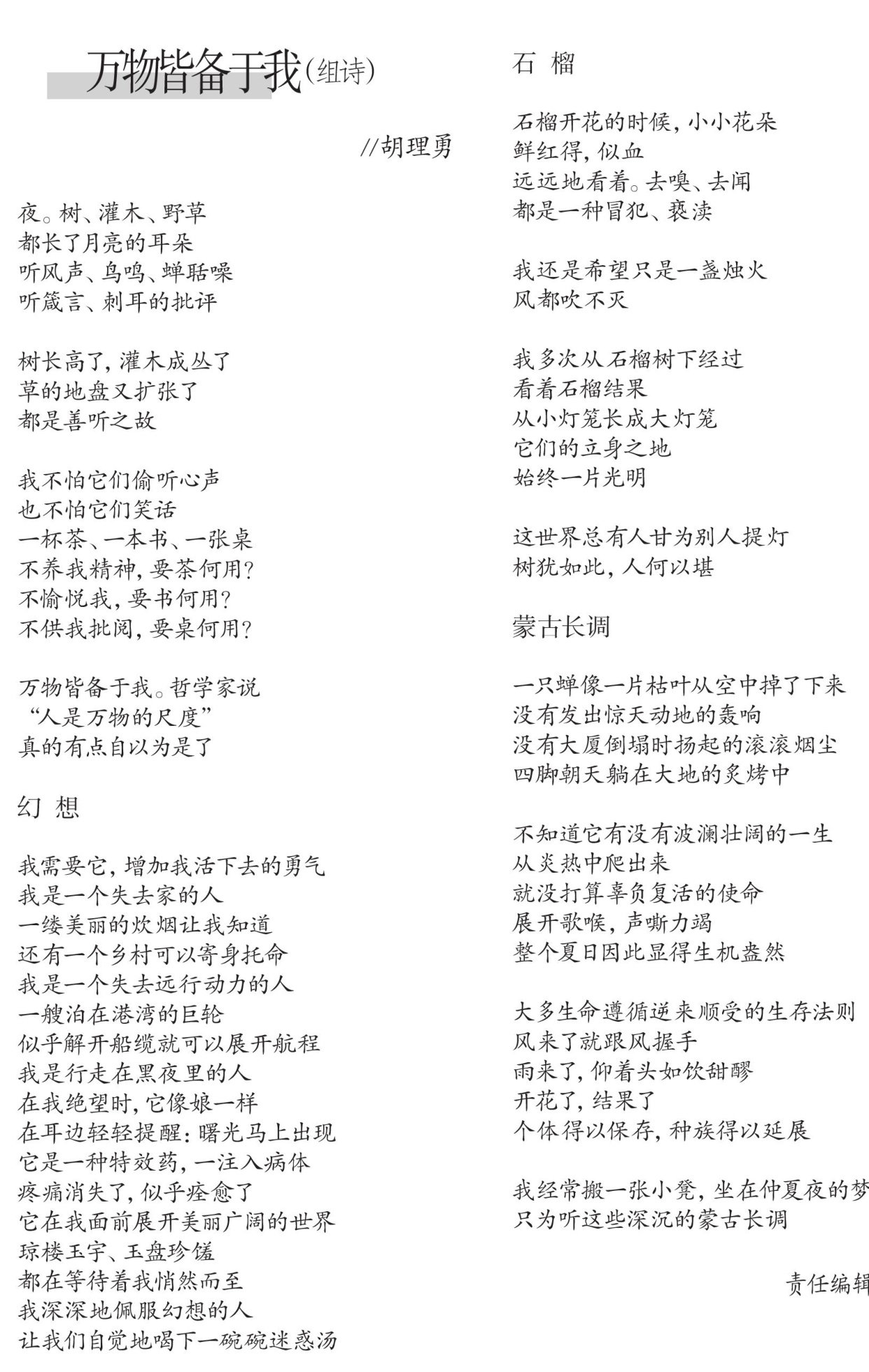
诗歌 | 万物皆备于我(组诗)
诗歌 | 万物皆备于我(组诗)
-
诗歌 | 房子是一种植物(组诗)
诗歌 | 房子是一种植物(组诗)




















 登录
登录